➤一部遲到的小說
陳栢青:明偉的新書《槍強搶嗆》寫宜蘭頭城的一場選舉。整本書裡敲鑼打鼓多熱鬧,子彈、栽贓、各式各樣的詐騙,還有陣營搶人脈送現金,你聽過的所有選舉中可能發生的骯髒、好玩、有趣的事情,都寫在書裡。
我覺得這樣的題材早該有人寫了,可是大家回想一下,你們有看過選舉小說嗎?我們這麼熱衷選舉,可能都出入過各種各樣的選舉場合,讓一個人上台,讓另一個人下台,但奇怪的是,文學作品中似乎缺少這一塊。所以明偉這本書非常重要,他補足了這一塊。
連明偉:其實不管是選舉或文學,甚至身處任何情境,有件事情非常重要,就是必須釐清關係和關係之間如何相互影響。我們如何從各種關係的糾纏中,重新找回自己。
我在構思這本書的時候,對於文學抱持一些質疑,根本的原因,很像栢青提到的:我們的生活不是正在選舉跟罷免,就是準備走向選舉跟罷免,文學是否有辦法介入?4年一次大選,再加上地方選舉,也就是每兩年就有一次重要選舉,這種選舉的節奏,大幅度影響生活,只是為什麼文學圈沒人處理這一塊?
文學必須做到的基本面向,是審視當代社會發生什麼,影響什麼,嘗試破壞或努力開創什麼,從中延展我們究竟可以如何改變。當代很多作品都以議題作為創作主軸,這些議題的記錄與創作,努力呈現社會各個階層各處視野,都相當重要,只是直接關係到我們生活本身的部分,似乎有些隱而未顯。當我嘗試進行填補,發現自己所處理的,表面看起來像是選舉,實際卻指向政治和權力。

➤趨近現實的複雜面,突破既定美學的創作嘗試
連明偉:我很早就想書寫這則故事,然而花了很多時間準備,才有辦法動筆,主要的原因是發現自己不夠理解這一切。那要如何突破呢?我想,只有真正親身見證,踏入被各種口號包圍,語言不斷被肆意浪擲的現場,那是各種形式的鋪張,以及意義的扁平與貶值。
選舉讓我們看到的,無非激情一面,但選完之後要用怎樣的眼光、怎樣的標準重新審視這些話語、承諾與政見?待在宜蘭鄉下,會遇見非常多古怪的違法事件。比如擄鴿勒贖、分銷走私充公的贓物,樁腳賄選就更不用說了。這些光怪陸離的事實,生猛草莽的行徑,並沒有出現在文學之中,鮮少有創作者處理,讓我覺得非常疑惑。
文學跟我的生活之間,產生極大距離,我們是否投注足夠心力,嘗試理解生活的場域?我想做的,就是大膽突破已然承接的美學。
美國作家強納森・列瑟(Jonathan Lethem)有一句話是:「讓豹群進來。」任何的創作都必然帶著極大的風險,你必須承繼過往的美學,同時設法突圍。所有的衝撞勢必走向破壞,承擔的風險在於,當代的人可能難以接受。然而如果要讓文學充滿可能,一定要有嘗試的勇氣,同時必須做好失敗的準備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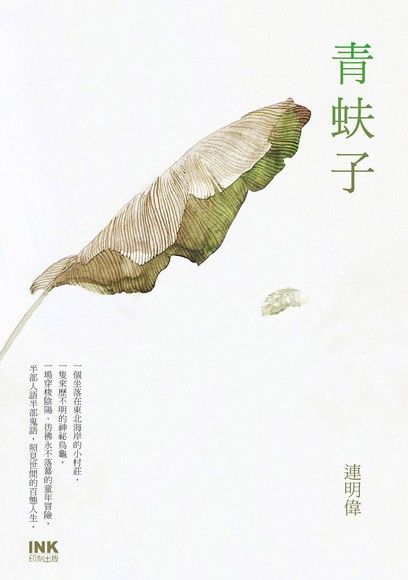 記得十幾年前寫《青蚨子》時,我在書中用了非常多的台文,必須面對的,就是讀者對於方言的本能抗拒。我覺得這是創作的可貴之處,勇於挑戰既定的準則,質疑已被形塑的意識,努力實踐篤定的想法――創作者應該嘗試走在前面。
記得十幾年前寫《青蚨子》時,我在書中用了非常多的台文,必須面對的,就是讀者對於方言的本能抗拒。我覺得這是創作的可貴之處,勇於挑戰既定的準則,質疑已被形塑的意識,努力實踐篤定的想法――創作者應該嘗試走在前面。
我們思考一件事情,一定會有各種不同的切入角度,就像我們看同一場選舉或同一政治人物,大家的觀感可能完全不同。我們很難否定自己心中認定的片面真實,對於某一事件、人物、形象,大家都有各自的詮釋、有不同投射,只有在創作中容納這些歧異的想法與價值,才能逐漸靠向實際社會的複雜面貌。
➤小說的預言性與語言的魔力
陳栢青:我在明偉這本書出版前3個月讀到時,大驚失色。因為這是我心中好想寫的東西,可是我無法寫出來。我就是那種關在書房的作家,和生活總是隔了一層,每天只關心娛樂新聞(笑)。
這本書的各種素材,都需要作者長期在生活中跟很多人來往,同時知曉各式各樣的價值、人情的酬酢。要在這種混雜的空間中,才能夠把這個社會各種好壞訊息全部收納於一點,再把它鋪展開來,最後變成這本小說。
我看這本小說真的是瞠目結舌,因為裡面的故事太誇張了,真的會發生嗎?一邊這樣想,轉開電視發現新聞內容也是這樣報的。小說好像預言了政治,小說寫出現實的內在層面,而現實則把小說情節演示得更誇張。
另一方面,讓我真正訝異的是本書的語言。大家在成長過程中,是否聽父執輩說過:「政治很髒不要碰,你只要專心讀書就好」?我就是在這樣的家庭長大的。但後來發現,政治無所不在,政治就是你的生活。
我第一次感受到這件事情,是因為一本雜誌上的宣傳。1996年《熱愛雜誌》創刊,是台灣少有的同志雜誌。那年我只有13歲,像買小黃書一樣去書局偷偷問:「你們有賣『那個』嗎?」藏著掖著,翻開前幾頁,赫然見到民進黨文宣光明正大登在上面。文宣言簡意賅,詳列出民進黨曾經替同志爭取過什麼:「唯一將同性戀議題放進總統選舉政見的,是民主進步黨候選人。率先為同性戀人士舉辦國會公聽會,支持同性戀人士權益的,是民主進步黨的立法委員……」
那時才幾歲的我,根本看不懂這些話是什麼意思。但文宣的最後一句話永遠打動我:「民主進步黨,是同志的同志。」
政治上稱呼夥伴為同志,然後這個同志也被挪用為同性戀彼此稱呼的代號。政治的「同志」和性別的「同志」有所連結,這時,政治跟性別就發生了意義。我們開始因為這個意義的發生,轉而對另一個跟我們本來不相關的事物,滋生莫名好感。
你可以說,從那刻起,我就因為這句話而成為「同志」了。只要能操縱語言,就能操縱人心——我們真的是透過理性在思考與投票的嗎?其實不是。我們心裡燃燒著一把火,想要對世界更好,可是這把火到底有多少材薪是真正經過理性思考?我不知道。
選舉變成控制人類心靈的遊戲,所以我特別在乎明偉怎麼寫選舉,怎麼去把那些選舉內裡的故事寫出來。
其次,我想看到作家如何操控語言。明偉一方面使用文學的語言,用很有破壞性的方式打亂語言的排序,另一方面又引入非常多的選舉語言。所以看這本書會覺得非常陌生,那是文學在發生作用。可是陌生之後,又會覺得非常親切,因為裡頭動用了非常多選舉語言的話術。
我想知道,你在裡面用了哪些選舉的語言?你如何去拆解選舉的語言,並且把它巧妙用在小說裡?

連明偉:語言在小說中的作用,基本上就是美學的實踐、藝術的表達,同時也是權力的體現。不同的身分位階、教育程度和文化養成,往往形成不同的語言系統。這本長篇小說的不同篇章,努力展現的動能,就是嘗試表現出小說具有不輸給影視的力量,這個目標必須透過語言和情節完成。
這幾年待在頭城,我有很多機會和長者互動。不同歲數、不同領域和不同的社會位階,會有各自的獨特話語,例如俗諺和行話。當我們觀察不同話語,嘗試解析,會發現其中隱藏著權力關係。思考選舉的時候,我發現書寫的並非只是選舉亂象,而是涉及權力,隱藏的權力制度以潛在的動能,不斷建構我們的思考。
面對選舉,很少人主動檢驗當選者:他們承諾過什麼?是否實踐政見?抑或選前語言只是一閃即逝的煙火?甚至即使知道對方講的是謊話,也有可能因為政治傾向,或因為某種認同,最後不得已予以妥協。
當我們要認真檢視,往往會被挪移焦點。例如,當候選人或當選者發生醜聞,只要推拖說這是不同陣營的惡意誣陷,就能變成清白之身,這種抹黑造謠的說詞,成為政壇的萬靈丹。
文學必須容納不同觀點,由此進行多方辯證,而非給出簡易答案。社會中的各個族群,擁有各自相異的政治傾向、利益關係和關懷次序,各自運作的思考,又潛藏怎樣的立場、預設與局限?
回到語言。基本上,話語的掌握與表達,就是權力與權力場域的隱喻,人們擁有多少發聲權,代表個體在社會位階的某種地位。然而,平日不常受到關注的族群,他們也有自己的言說系統,只是我們往往視而不見,或者將之貶抑,這其實相當殘酷。
➤期待更多政治文學作品
前幾年我在歐洲跟一些藝術家聊天,大家討論到對自己的創作而言,哪一件事情最重要,或者具有根本上的影響。對於英、美或加拿大這些大國創作者而言,愛情、友情和親情非常重要,政治永遠是放在很後面的事。可是我們臺灣人,或者一些小國創作者,無論書寫什麼題材,始終無法避免政治思考。
![]() 台灣的選舉小說不多,我讀到覺得滿不錯的作品,像是新世代重要作家洪明道,他的小說集《等路》中有一篇〈村長伯的奮鬥〉,寫得非常好,掌握地方選舉的人情、人性與真假辯證。
台灣的選舉小說不多,我讀到覺得滿不錯的作品,像是新世代重要作家洪明道,他的小說集《等路》中有一篇〈村長伯的奮鬥〉,寫得非常好,掌握地方選舉的人情、人性與真假辯證。
選舉小說雖然不多,但是我們有許多政治小說,或者明顯充滿政治意義的小說。作者可能參與過某些政治活動,或者以議題方式肉身搏鬥,最後反芻經驗。
國外有比較多選舉小說,像是奈波爾的《艾維拉投票記》,描寫加勒比的千里達,書寫小國剛開始施行民主選舉時的亂象、荒謬和根深柢固的迷信。此外,我極度推薦大家去讀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的《投票記》。這本書不僅有趣,同時充滿諷刺。
一場選舉的開票結果,70%的人都投了廢票,政府決定進行第二次投票,結果空白票往上攀升至80%。簡單而言,小說表達對於政權、候選人和制度本身,投下不信任票。薩拉馬戈透過這本書,演繹人民的另一種權力,同時拋出對於體制的質疑,部分情節甚至符合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許多現實情境,小說成為珍貴的預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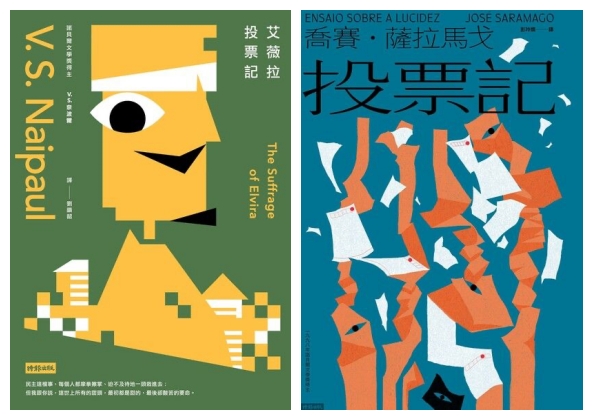
至於我的這本新書,想做的不只是闡述台灣的地方選舉,更是透過4個迥異系統,包含相異的語言、詞彙與敘述風格,以不同位階的角色相互發聲、彼此共匯。
第一則中篇是在地年輕人,待在鄉下看不到未來,一天領個1000塊左右,幫忙造勢,對他來講最重要的就是賺錢過日子。第二則中篇是從外地來的中年女性,刻意假冒宜蘭人,待在競選人身邊策劃整場選舉,迷惑人心,抓住選票,以此獲得豐厚報償。
第三則中篇是在地樁腳,一位老婦人,寫她如何籠絡民心,如何花錢買票,如何在選舉中榨取利益。第四則中篇,透過一位中年人視角,談論如何看待整場選舉,如何用清晰眼光審視整起事件。
第四篇最難寫,因為自己有太多話想要訴說,也因為過於靠近,沒辦法讓小說結束,彷彿想要透過書寫讓鄉土成為淨土——即使知道那並不可能。
台灣鄉下因為人口老化,有些長輩覺得自己年紀大了,還需要思考台灣的未來嗎?何必想得太遠,只要顧好眼前的生活就好。當我們嘗試溝通,往往會遇到各種挫折。溝通是一種軟性說服,然而當你在講述道理時,不能讓人感覺到要被說服的壓力。你想透過文明的方式溝通,但對方想的可能是下一頓飯要吃什麼。對他來講,看重的是個人的即時利益。日積月累後,這一切很可能就會變成世代之爭。
觀察地方選舉,可以看到社會被隱藏起來的另一面貌,小說的書寫,就是想要補足這些觀點,用不同的視野切入。如果沒有透過多元複雜的角度審視,文學便無法呈現表層底下的真正真實。
➤政治語言是選舉的藝術,文學語言是獨厚失敗者的藝術
陳栢青:我有個怪癖,就是收集選舉語言,但我搜集的是敗選宣言。轉台到敗選者陣營,比看人勝選還開心。
我曾經懷疑自己是不是只想看別人摔跤,後來發現不是,我真正在意的是輸家怎麼辦:他們怎麼面對人民的選擇?怎麼宣告輸了?怎麼去安撫他的選民?怎麼安慰自己?怎麼為自己的失敗找個理由?
勝選感言常常只是個儀式,作為選舉的結束。而敗選感言往往不只是儀式,它暗示下一次選舉的開始。
我覺得這就是民主的真諦:並不是失敗了就永遠離開這個舞台,你永遠可以跟人民溝通,永遠有「我將再起」的機會。這時候語言得到了另外一種轉化;如何掌握語言去切入權力,甚至改變權力的結構,這都是選舉的藝術。
我想再問明偉一個比較難的問題:你的小說語言要如何對決選舉的語言呢?你覺得你的文學語言有勝利嗎?
連明偉:這是相當艱難的一件事情,一如要用文學去對抗虛假。我非常喜歡作家哈金的一段話,他說,小說的作用,是要讓小說變成永恆的社會新聞。如何讓小說變成永恆的社會新聞?必須透過文學技術。
所有的選舉語言都有虛假的一面,然而我們不得不容忍,甚至不由自主希望這些虛假之中,某部分可以成真。也就是說,我們允許謊言,知道承諾極有可能不會成真,但我們願意相信或許有成真的可能。
這跟愛情非常像,我們看到的這些形象、聲音與作為,帶有鮮明的廣告成分,必須要讓民眾相信人設,才有可能獲得選票。文學可以做的,就是用理性思維進行解構與建構。短時間之內,我們可能不知道什麼為真,什麼為假,什麼可以確切實踐,但是我們可以永遠相信文學――特別是帶有批判意識的文學。
陳栢青:明偉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,說到底,文學是語言的藝術,但它又不只是語言。正是因為文學,它讓我們得以去檢驗物事的真假,包括語言自身。
如果問我這個問題,對我來說文學是獨厚失敗者的。日本作家川本三郎曾說:「文學,只有文學,可以側耳聆聽挫敗者的輕聲細語。」這段話非常感動我。敗者也有心,也有他的尊嚴和不容忽視的理由。文學替他們留下空間。文學讓我們可以跟他們同理。文學告訴我們,聲音不是只屬於勝利者的。
同樣的,政治不應該只屬於勝利者,我以為政治最理想的一部分,應該和文學一樣:「創造一個對話的空間」。說到底,無論文學或政治,誰會是最後的贏家?我希望是你們,也希望是我們,希望是我們所有的人。投出那張票的人,會是最後的贏家。●
|
作者:連明偉 |
|
作者簡介:連明偉 1983年生,暨南大學中文系、東華大學創英所畢業。曾任職菲律賓尚愛中學華文教師,加拿大班夫費爾蒙特城堡飯店員工,聖露西亞青年體育部桌球教練,現為北藝大講師。著有《番茄街游擊戰》、《青蚨子》、《藍莓夜的告白》、《山與海的職日生:頭城職人誌》等。 |




